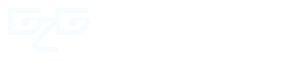平台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最高法案例为您划定红线
平台用工模式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究竟是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如承揽、居间),还是不平等的劳动关系。这一认定直接关系到平台是否需要承担《劳动合同法》下的一系列义务,如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支付加班费、遵守解雇保护规定等 。由于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成为了划定界限的关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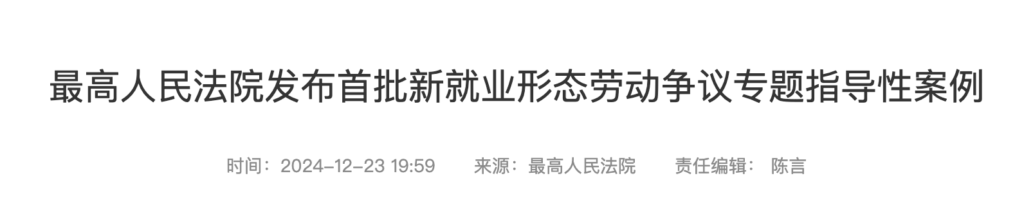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普遍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不会仅仅因为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或“承揽协议”就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相反,法院会综合审查一系列要素,以判断平台对劳动者是否存在支配性的劳动管理 。
“支配性管理”的认定标准:一个多维度的光谱测试
最高法的指导案例显示,法院并非采用非黑即白的标准,而是进行一种“光谱测试”,综合评估平台管理的强度和性质。以下是从案例中提炼出的关键判断维度:
- 业务的整合程度: 劳动者提供的工作是否属于平台企业核心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外卖骑手的配送工作,被认为是外卖平台或其外包公司主营业务不可或缺的一环 。
- 管理与规制的强度: 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是仅仅为了保障服务质量而进行的“必要运营管理”,还是深入到工作过程、行为规范的“支配性劳动管理”。
- 强支配性特征: 平台制定详细的工作规则、奖惩制度、服务标准;通过技术手段(如APP)对劳动者进行持续的监控和指挥;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地点、方式、价格没有实质性的自主决定权。
- 弱支配性特征: 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何时上线;可以同时在多个平台工作;对服务价格有一定议价能力;平台管理主要以结果为导向,对过程干预较少。
- 经济依赖性: 劳动者是否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单一平台,其劳动报酬由平台单方面确定和支付。
- 生产资料的归属: 劳动者是否需要自行准备核心的生产工具(如车辆)。但这通常不是决定性因素。
- 规避法律的意图: 法院会特别关注平台是否存在通过复杂合同安排(如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签约)来刻意规避法律义务的行为。这类安排往往会被视为无效。
案例深度剖析
- 指导案例237号(外卖骑手案):劳动关系成立
- 案情: 外卖骑手徐某与某服务外包公司签订承揽协议,但该公司实际上承接了某网络公司的商品分拣配送业务。徐某的工作受该公司规章制度约束,报酬由其按月支付。
-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徐某从事的配送工作是外包公司的核心业务;他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和纪律约束,在人格上具有从属性;报酬由公司稳定支付,在经济上具有从属性。因此,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构成劳动关系。
- 指导案例238号(“个体工商户”骑手案):劳动关系成立
- 案情: 某网络公司要求外卖骑手圣某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与其签订合作协议。
-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这种模式是平台为规避用工主体责任而采取的非正常用工方式。圣某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报酬标准均由平台实质性决定和控制,双方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 指导案例240号(代驾司机案):劳动关系不成立
- 案情: 代驾司机秦某在平台APP注册,可自由抢单,平台对其进行必要的服务规范管理,如着装要求、服务流程等。
-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平台对秦某的管理属于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和商誉而进行的必要运营管理,而非支配性劳动管理。秦某在工作时间、接单选择上有较大自主权,与平台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故不认定为劳动关系。
对平台企业的合规建议:
- 精准定位用工模式: 企业应根据自身业务和对劳动者的管理强度,清晰定位自己的用工模式。如果管理强度高、劳动者自主性弱,则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风险极高。
- 审慎设计管理规则: 在制定平台规则时,应尽量避免对工作过程的过度干预。将管理重点放在服务标准、安全要求和结果评价上,而非考勤、工作纪律等传统劳动管理手段。
- 避免无效的规避行为: 强制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明显的规避行为,在司法上已难获支持,反而可能因恶意规避而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
- 探索多元化保障体系: 对于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合作者,企业也应积极探索提供商业意外险、职业伤害保障等多元化保障措施,履行社会责任,降低运营风险。